斗罗大陆免费观看265集预告 斗罗大陆第265集:唐三碎骨弑神,小舞血翼焚天泪淹嘉陵关
斗罗大陆第265集:唐三碎骨弑神,小舞血翼焚天泪淹嘉陵关
大家好我是少军,这期分享《斗罗大陆》第265集:双神黄昏!唐三碎骨弑神,小舞血翼焚天泪淹嘉陵关
复活吧!我的爱人——” 神王泣血撕裂魂环,十万年柔骨兔燃烧宇宙最后光焰!
1. 「海神崩殂
唐三自碎海神神装!**百万块神器碎片化作星辰暴雨,贯穿罗刹神比比东胸膛——弹幕炸屏:“神器碎时全场泪崩!”
*特效高光:碎片折射出小舞献祭、星斗求婚等回忆杀,每一帧都是刀片*
2. 柔骨焚神」
小舞献祭终极版!九红金环融为血翼以肉身硬扛天使圣剑,嘶吼响彻云霄:“哥,这次换我守护你!”
*高燃镜头:血翼焚毁时飘落的兔耳绒羽,在火光中凝成“相思断肠红”虚影*
3. 「罗刹真容
比比东神铠碎裂露真身——**千疮百孔的躯体爬满噬魂黑虫**!临死前幻见玉小刚,指尖未触便风化:“这一生...错付否?”手握修罗血剑,我便是善恶准则!”**
>——唐三左眼海神蓝右瞳修
罗红,双神位爆裂碾压神界法则!
> **“武魂帝国?笑话!你听听——这山河姓唐还是姓千?!”**
> ——昊天锤轰碎天使神像,唐昊于残垣中举起猩红巨锤!
·新纪元开启
- 史莱克七怪神光加*:奥斯卡食神菜刀劈开神路,宁荣荣九宝神塔镇山河!
- 千仞雪神格碎裂:堕入黑暗前嘶吼“唐三!轮回尽头必杀你!”(**白发黑翼魔化造型**伏笔)
- **深海魔鲸王残魂反噬**:唐三右臂突现**克苏鲁式触手鳞纹**!
---
> “小舞血翼挡剑瞬间,**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哭成狗**”
> “比比东幻灭那幕封神!**原来终极BOSS渴求的只是一句‘值得’好了这期分享到这里,有喜欢的点个关注,有不同意见的在下面讨论。
相关问答
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神念结晶诺丁城区在哪??-ZOL问答
5条回答:斗罗大陆里,史莱克学院的神念结晶在地图上分布很广,得去指定地点获取。不少玩家想知道其具体位置,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神念结晶的位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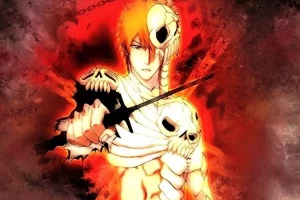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